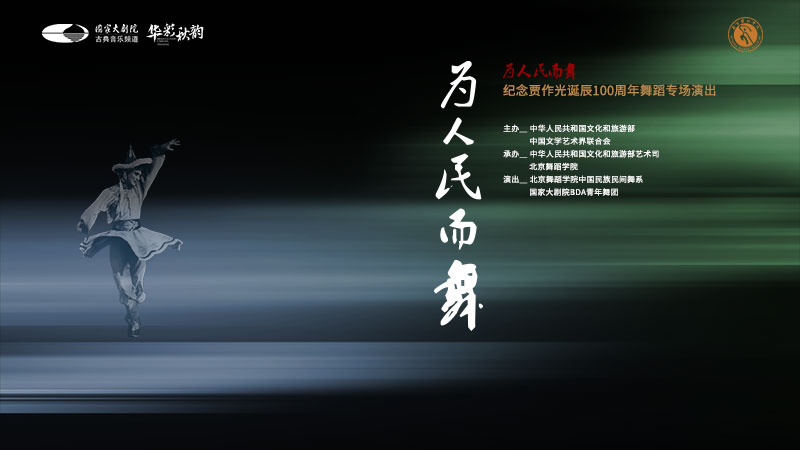(作者 Sofia)面对郑天玮的时候,很难想象她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已是第30年。这个性格十分爷们的女人丝毫不避讳年龄,在演员与编剧的双重身份间自由切换—19岁进人艺的她演过曹禺的所有戏,比如《茶馆》的四凤、《日出》的陈白露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角色,还将陆续出演人艺重排的获诺贝尔奖的著名剧作中的女主角;而作为人艺一级编剧,她又写下了《古玩》《无常·女吊》等叫好又叫座的名剧,4月19日登场国家大剧院的大型原创话剧《王府井》也出自她手。
虽说郑天玮本是苏州人,但因为在部队大院长大和在人艺浸淫多年的缘故,她更像个地道的老北京。为了写横跨百年历史的《王府井》,郑天玮在这条街上游荡了好几个月,从太阳尚未升起一直到夜里人影匿迹。她说她是在慢慢感受、认识它,试图还原它过去的样貌,正是这段经历催生了剧中魔幻一般的人物“匾爷”。“就像我台词里写的,这条街你要不认识它,它也不认识你,你怎么在这里站着?要去认识,就像象征传统的匾爷说的,只要你心里有我,我就在这;只要你想得起我,我就陪着你。”
初见郑天玮便可以感受到她旺盛的精力与自信,说话铿锵有力,甚少犹豫。这股子精气神多半来源于她的演员经历,11岁在铁路文工团是专业的舞蹈演员,19岁进了人艺,到现在整整30年。1995年郑天玮开始写话剧《古玩》,然后就调入人艺创作室当起了职业编剧,她觉得是自己命好,“其实一直都挺顺的,比如说《古玩》集合了北京人艺所有最优秀的导演、男演员,我做音乐剧、做5·12地震的话剧《生·活》也都是最好的人在合作”。
到2000年她又回去演新版《日出》,当完陈白露后创作《无常·女吊》,写完《生·活》演《龙须沟》,演完又回来写《王府井》,无形中就开始写一个演一个。这样演员—编剧、编剧—演员的切换,就算精力充沛如郑天玮也觉得有点分裂,需要外放的演员与需要内敛的编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但她愣是玩儿得风生水起。她说自己以前的性格并没有这么外向,是在写《古玩》的时候,常常凌晨四五点去潘家园的鬼市,和那些进行古董交易的商贩打交道,积累素材,所以不得不厚着脸皮豁出去了。
问及哪里来的勇气接下很多著名男编剧都不敢碰的难啃题材,郑天玮说没想那么多,全凭一股冲劲,认定了目标就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去做,反而结果都不错。其实她写的戏从2007年到现在有十几部,但并不是写完就马上排,会等有合适的班子再排,比如《无常·女吊》的下部就早已写好。而她在《王府井》后又要在国家大剧院演获得诺贝尔奖的剧目《榆树下的欲望》。
采访: 《周末画报》×郑天玮
从演员到编剧
您从演员改行当编剧时有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没有,第一个写的《古玩》,当时是自己申请想做的,我们院长也很看好我。那个时候我已经经常发一些比较短的文章还有诗,做了很多文字工作,当然不是平地就说要写剧本。但是首先我对古玩不是很了解,只是对这些人比较感兴趣。当时我还比较腼腆,去采访的时候会被拒绝,后来就慢慢克服心理障碍,就硬扛着豁出去了。其实我当时就是喜欢编剧就冲着这个事去了。
从《古玩》开始你写的戏都是很难啃的大部头,怎么坚持下来的?
像这次的《王府井》,大剧院优秀的工作人员都扑上去做,我肯定也要扑到战壕里。有时候工作环境特别重要,在一个大师聚集的剧院里,你必须不能懈怠,全心去做。我觉得努力很重要,需要有奋斗的精神,还好每次结果都比较乐观。比如《无常·女吊》,根本没想到最后票会都卖光,观众都坐到过道上了。有天我到小剧场看大家拿着报纸在排队,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票都卖完了,没办法,剧院工作人员只好把报纸撕了卖过道上的票。《古玩》也是,离演出还有7天票就卖完了,门口挂着牌子说已售罄,票贩子不信,把我们剧院售票处的玻璃窗给砸了,还扇卖票的人一嘴巴,北京台还做了新闻报道。
你写剧本时是一个什么状态,会自己跟自己演吗?
我不喜欢用电脑,都是手写剧本,会一边写一边自己叨咕台词是不是顺畅,以免写成书面语。而且我特别不怕吵闹的环境,经常放着《喜洋洋灰太狼》当背景声写。
《王府井》曾经写跑了几个著名编剧,你有没有写崩溃的时候?
没有,它已经变成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最近跟国家大剧院的陈院长说,我现在都改上瘾了,每天不做这个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整个人都爱上这个东西了。我特高兴干这个事,也很感谢《王府井》,提供我重新学习、重新看待历史的机会。这不是简单写个戏,它对我的一生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影响我后半生的其他创作。整个过程要看北京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就像重新上了次学。
关于话剧《王府井》
《王府井》这个戏是上下部,分别是两个半小时。1900-2010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浓缩在这5 个小时里,你如何做取舍?
先说一个硬框架,全剧分清末、民国、抗日、解放、文革、改革开放六段。其中的四条线索是:民族之内人们自身的斗争、资本主义强势进入的民族斗争、闭门锁国的民族内斗争、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以另一种力量进入,形成了一个扭动的力量,一个悲剧的力量。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悲剧就是最大的悲剧。这个戏不是写一店一铺的兴衰或者某个商人的发家史,而是整个王府井为载体的整个北京、整个民族100多年里的兴衰。其实是有悖话剧创作的,比如说话剧的三一律。这是这个戏比较难解决的问题。选取的必须是比较大的事件才能跟所有人有关系。比如第二幕,1912 年曹锟的大火把整个王府井烧毁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商人没有倒下,他们成立了商会重新崛起了王府井,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帮商人太伟大了。
所以商人是这个戏的重点?
王府井是条商街,当你重新回头看,为什么这条街无论经历多少次的劫难依然在?就是它遵循着“守德不守财”,这是我在戏里不断说的东西。连里面的太监也会说出“用我这条没根的命换老祖宗这条有根的街”,可以看出这条街本身具有的灵魂。它不是简单的一条街,这就是为什么这条街能成为中国人心里的一条金街。
即将上演的是《王府井》上部,那么下部大概什么时候完成?
不出意外的话年底。上部是生编,下部是带有基础的编,但是后面带有政治背景的东西太多了,比较敏感。但是我坚决不躲着走,我希望又能审得过又能让百姓们看得懂。
比如当时公私合营让很多老字号生存不下去了,会有这段吗?
必须有,全部都是硬碰硬的。整体肯定是悲怆的,史诗般力度的。过去人家说北京人就是吃喝玩乐,但是我觉得北京人有激情勤劳包容的一面,有他的长处。
你自己比较满意的台词或者戏?
有意思的可能是比较核心的东西,比如当时国民党逃走时匾爷还在这条街上,有人问他现在只有关门的没有开店的,你这匾刻给谁?匾爷说“我刻给我自己”。上半部结束时匾爷手一挥,刻出满台的一个王府井。所有其他的匾都悬下来,然后匾爷和一个小伙计在雪地里向王府井这个匾和几十个其他的匾行大礼,比较升华。
你自己不演?
我从来不演自己写的戏,我不信(自己编的)就没法演。
“我就是王府井的匾爷”
请讲讲《王府井》中“匾爷”这个角色。
故事总得有个牵线的人,就像《茶馆》里的王掌柜,牵出各色的人。而匾爷是王府井的精神象征,是传统的灵魂象征,是人物内心的外化。他不是串场,他在人不能说话时说话。这是我们的新尝试,是诗意的现实主义。他嘴里说出来的词有很神的,也有很朴素的。比如说一幕结尾时他说“不顾满城飞炮火,深宫犹自赏神灯”。也有插科打诨的时候,游荡在街上。
你是怎么想出这个人物的?
因为我游荡在这条街上。我在北京人艺上下班都要经过这条街,但当你领了这个任务后发现还是不认识,要重新去看待它。
你之前对王府井的认识是什么样的?
从前就是我上班的一条必经之路。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东安商场,卖果脯柜台的营业员常往果脯上泼蜂蜜水,我趴在玻璃柜外看那些亮晶晶的果脯,觉得特别神奇,特别诱人。去一趟就非常高兴。当时人特多、路特窄,但那个时候感觉王府井特别大。当时跑王府井就意味着进城,头天就得想向家里人要什么东西,还得编出很多想法来。
你“游荡”在各个老字号时,收集到了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在圣禧福帽店里,我发现有种绒毛的东西从没见过,他们说这叫作海龙,它在水里很深的地方。那时根本没法抓那个东西,所以海龙金贵就因为里面包含了人命。捕海龙必须有杀父杀子之心:冬天人把冰凿开,喝很多白酒,躺在冰上等着。海龙从那个洞里上来,看你快死了,过去暖你,而你则要把它扎死。刀如果稍微扎不准,用力过大的话就可能掉进冰水里冻死。我在写剧本时借用这个故事,写了老掌柜的两个孩子被太监逼着去捕海龙。但是因为这个戏很重,我会用一些喜的点放在里面,不会让观众觉得整个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