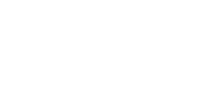我想先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听众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想是因为听众的欣赏水平在提高。按道理说,肖斯塔科维奇也是二十世纪的作曲家,可以划归为现代主义作曲家。如果是在50年前,我们也许也接受不了他的作品。然而随着我们接触和聆听到了更多的音乐,听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深度都在提升,过去接受不了的东西慢慢变得可以接受,所以才显得肖斯塔科维奇是“最后一位”古典音乐作曲家。也许再过30年,这个看法会改变。
第二个问题:肖斯塔科维奇在西方音乐史的地位。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所谓肖斯塔科维奇音乐的专家,只是我相对其他中国指挥家来说,演出他作品的次数最多,也自然在不断接触中自然了解得更深一些。我个人认为,肖斯塔科维奇是二十世纪近代音乐史中最伟大的一位作曲家,原因有三:
首先,与他之前的作曲家相比,肖斯塔科维奇独特的音乐语言、和声、曲式结构以及他对音乐内涵的挖掘,是到了新的深度和层次的。其次,与他之后的作曲家,比如梅西安、利盖蒂等人相比,他的音乐更加有人情味,更能够被普通听众所接受。我认为一部没人演奏、没人聆听的作品就等于是仅仅存在于谱面上的符号,就像一把顶级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如果不用来演奏,只能看做精美的木头,那将是没有生命力的。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恰恰是可听性很强的,在旋律性上是更具有亲和力的。第三,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他的作品内涵很深,包含了十分浓郁的人文情怀。在他的作品中你能听到非常强烈的爱、恨、彷徨、愤怒、抨击……几乎包含了一切人类的情感,并且把每种情感都做到了极致。反观二十世纪的其他作曲家,从之前的普罗科菲耶夫,到之后的潘德列茨基,他们的作品都更偏理性,更注重形式之美。我不否认形式美的重要,但在听众的接受程度上,他们的确没有达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程度。
即使将尺度放宽到整个西方音乐史,能兼具以上三点的作曲家也不是很多,所以我认为肖斯塔科维奇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
答: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讲一个艺术作品的欣赏方式,我时常建议一个乐团或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在试图真正了解一位作曲家的时候,将他最早期的作品和最晚期的作品放在一起对比聆听,也就是从两端去感受,然后慢慢“填满”中间的作品。不仅局限在音乐中,其他的艺术门类也可以做这样的尝试。
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去观察贝多芬,就会发现他的创作几乎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过程:从第一交响曲的简单淳朴,到第九交响曲的宏伟庞大;歌剧大师威尔第也是如此,从开始的《奥尔贝托》、《纳布科》一直到无比壮丽的《奥赛罗》和《法斯塔夫》。相比之下,肖斯塔科维奇的这十五部交响曲就不是这样,我将其形容为“波浪前进、螺旋上升”。
他的第一交响曲,充满朝气,音乐语言也非常朴素,随着他越来越多地受到近现代作曲技法的影响,他开始希望自己能有新的突破,第四交响曲就是这个突破点。这部作品结构极其庞大,音乐也晦涩难懂,自诞生之日就遭到了舆论批评,甚至在长达25年的时间内被禁止演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挫折,从高峰跌入谷底。
第二个上升期就是从第五交响曲到第九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重新调整了自己创作风格,同时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所谓“时势造英雄”,在残酷的战争中,在直面生死离别的场景中,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创作热情被最大限度的调动,也写出了“战争三部曲”(即第七、第八、第九交响曲)。
接下来的第十到第十二交响曲可以被看作平稳的“低段”,而第十三、十四两部交响曲则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觉得这是整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交响曲,创作技巧达到了巅峰。此时的肖斯塔科维奇已经完全摆脱了第一、第五、第七交响曲的那种相对通俗的音乐语言。在这之后,一个“断崖式”的下降,结束在第十五交响曲中。在这部作品里,病入膏肓的作曲家不得不直面“死亡”这一课题,参透人生的他回归最初的童真,运用旋律化的十二音技法创作,在童话般的弱奏中结束,仿佛走向天堂。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从无知到睿智,从幼稚到成熟,这个过程通常不是一路向前,而是充满反复的。在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写作的“三次波动”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些。
答:应该说第五交响曲是肖斯塔科维奇音乐创作中的“里程碑”,对他日后的创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我前面谈到的,在第四交响曲完成后,肖斯塔科维奇遭受了很多的攻击,比如批判他“走进了形式主义的误区”。作为一个内心敏感、自尊心很强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一定是痛苦的,他陷入一种挣扎之中。
在短暂的沉寂之后,他拿出了第五交响曲。这部作品的语言可能是他所有交响曲中最通俗的,但是请注意,“通俗”不等于“庸俗”,他并没有降低自己的音乐格调以及在创作上的孜孜追求。他还是想用抽象的音乐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这部作品仍然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
正如你提到的,它的第一乐章有一种愉悦的美,第四乐章结束在D大调上,在辉煌的号角声中呈现出一片光明,这都令它很容易被人接受。但是同时,当我们聆听它的第三乐章中大提琴与低音提琴充满张力的旋律,像鞭子一样肆意抽笞时,就不会再简单地把它看作是某种单一情绪的抒发了。在这些音乐段落中,我经常感觉到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像是鲁迅的文章,辛辣、犀利,同时充满了彷徨与苦闷。最终,这部作品也获得了斯大林的赞扬与肯定,为肖斯塔科维奇日后的音乐创作打开了一扇大门。
答:的确,第八交响曲和之前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太不一样了。第七交响曲充满了画面感,形象非常鲜明。乐曲伊始,壮丽的大调代表团结的苏联人民反抗侵略者,而当小军鼓敲响,猥琐、阴暗的敌人形象立刻出现,C大调的结尾象征胜利的凯旋……可以说是一部“爱憎分明”“善恶明晰”的交响曲。
但是在第八交响曲中,这些都被抽象的隐喻所替代。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已经浮现了胜利曙光,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到达了转折点。这时,肖斯塔科维奇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特质就体现出来了。他站在废墟上,思考的不仅是眼前的胜败存亡,而是整个人类为何会陷入这样惨烈的困境?庞大的第八交响曲充满了复杂的音乐技巧,比如高难度的赋格手法,还有大量复合拍子营造出的“舞蹈性”。他不是在玩弄技巧,而是试图在这种不平衡的音乐状态中描写“扭曲的美”,并以此代表人性扭曲、丑恶的一面。和第十五交响曲一样,第八交响曲以弱奏结束,但这个音符的消逝并非胜利在望时的欣喜,而是代表了我们要走向永恒的沉思。可以说,在第八交响曲中,肖斯塔科维奇站在了更高的角度关怀人类的悲喜命运。相比第五交响曲,无论是从演奏还是欣赏的角度,这部作品都需要我们多做些功课,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选择演奏这部作品,说明他们有勇气、有思想。
答: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交响曲是我在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的毕业演出作品。当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我指挥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奏这部作品。在我看来,这是一部真正的交响曲,也是最典型的“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在这里,作曲家完全摒弃了最初的情景描写、历史场景再现,或者是为了表示自我立场和态度而创作的想法。如果说在第四交响曲中,他对于技法和思想深度相结合的尝试还稍显生硬、导致作品的晦涩难懂的话,那么第十交响曲则完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这部交响曲的开头,是低音提琴演奏断断续续的旋律碎片,就像一个陷入沉思的人,想到了什么,却又忽然忘记了,整部作品就在这样模糊的引子中展开,可以说把人生的挣扎与磨难都写进去了,同时在和声、曲式等技法上也无可挑剔,完全符合交响曲的逻辑。你提到卡拉扬偏爱这部作品,我想这也是出于指挥家的综合考虑,他要选择适合自己发挥的作品,如果作品过于具象和明确,那就等于让诠释者“戴着镣铐跳舞”,所以一部无标题的第十交响曲,有理由获得青睐。
首先我觉得肖斯塔科维奇并不保守,我甚至认为他是那一时期所有苏联作曲家当中最富创新精神的一位。虽然他使用的创作体裁看起来很常规,但正是这种均衡、广泛的涉猎和尝试才让他的音乐自成体系,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很值得一提的是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大量的电影配乐,与他的芭蕾舞音乐和器乐独奏作品一样,这些音乐都非常出色,全面地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
具体说到《森林之歌》,这是一部清唱剧。有了歌词,当然就比纯音乐更容易打动人,也更好理解,因为作品要表达的内容直白地告诉了听众。正如你所说,这是一部讴歌胜利、赞美光明的作品,这与我们认知中那个充满忧思与苦难的肖斯塔科维奇的形象好像并不符合,但我觉得这并不矛盾。因为生活并不是永远在苦难之中的,这样的人生既不现实也很难持续,他的生命中也有欢乐。比如他写给自己的儿子马克西姆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就非常的天真、活泼,你能感觉到里面有一种慈祥的父爱。生活中的肖斯塔科维奇其实是一个很爱开玩笑、很幽默的人,只不过长了一张深沉的脸。
《森林之歌》是我担任上海歌剧院院长之后排演的第一部作品,我认为它的写作技法确实不俗,选择清唱剧的体裁配以积极向上的歌词,借用森林等意象来歌颂阳光、歌颂和平、歌颂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我相信他是发自内心的。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整个苏联在昂扬的斗志鼓舞下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奋斗,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是不应该怀疑的。
我很高兴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新的乐季中选择这样一部作品,因为肖斯塔科维奇的合唱写得非常好,音域的选择、设计都很适合合唱团发挥,而国家大剧院的合唱团又是国内最优秀的,相信这会是一次非常优秀的演绎。
答:正如我一开始讲的,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是对深切关注人类苦难、人文情怀深厚的人,也是心灵敏感、充满同情、嫉恶如仇、崇尚真善美的人。
我时常觉得我们所处的时代中,有太多的人被物质遮住了双眼。在社会经济飞速增长的形势下,炫富、攀比、拜金主义等等观念驱使下的现象也不断涌现,让这个时代显得有些混沌。也正因这样,我们国家自上而下开始注重文化建设,树立核心价值观,抵制低俗文化蔓延。我认为这都是极有必要的,因为一个民族是不能缺失灵魂和深层思考的。如果说娱乐节目可以简单地以收视率、发行量、票房来衡量,那么文化的建设发展则绝对不行!试想,如果我们一切以市场为导向,谁还去听、去演肖斯塔科维奇?谁还会静下心想一想人类的苦难、想想如何充实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干脆都走进体育馆,挥舞着荧光棒听一场热闹喧嚣的演唱会好了。这不是非要比出高和低,而是不同的艺术作品承担着不同的社会意义和功能。这个社会,这个时代,需要深沉的思考,需要肖斯塔科维奇!我也相信,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新乐季,会让那些有心灵追求的观众满载而归。
高建:乐评人,国家大剧院工作人员。
张国勇: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系主任,青岛交响乐团艺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