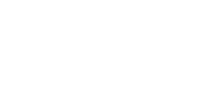答:其实大家对莫扎特可能有一种误解,觉得他的音乐太难,于是大家都在问:用什么方法演绎莫扎特呢?怎样去正确地诠释呢?但这样问可能是有点本末倒置了。莫扎特生活的年代是欧洲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变革时期,中产阶级在变革中逐渐兴起。虽然主导社会和精神的还是教廷和贵族,但中产阶级的崛起给了作曲家和演奏者一个非常大的平台。以前只是在教堂和贵族家里演出, 现在要到剧院里演出了——这就是世俗的音乐会。所以,莫扎特作品中的人文因素、世俗因素特别明显。从这方面来讲,莫扎特是很好懂的。 因为他不牵扯政治、宗教,他的音乐表现的就是我们人的生活。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懂得那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了解当时的历史、民俗和社会习惯。作为一个指挥,百分之九十的角色是作曲家原意的忠实传达者,比如音色和句法等演奏风格需要非常注意,在充分尊重总谱的前提下,才可以有个人的表达空间。我始终在强调,莫扎特、海顿所代表的古典时期的音乐其实最简单,就是需要将顿音、断音演奏好,将legato(连奏)做到极致。Legato就是歌唱,每个音都要唱好,力度要照谱子上写的做好,句子越大越好,不要小句子。和声丰满,声音好听,速度正确,句子大,legato(连奏)、staccato(断奏)做到极致,就已经具备了百分之八十了。此外我们再注意他特有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再现部和呈示部里出现的不同的变化,我们要问问:为什么会有不同?是他想吓唬你一下,或者给你一个惊喜,你把这个也做出来,就像模像样了。但是,难也就难在这一点,也就是越简单的越难。你刚才特别谈到“细节”,这很重要。如果能把音乐中的细节做到完美,把音色做到漂亮、有光彩,再把其他东西做到谱子上写的,那就一点都没有问题了。所以,就这些方面来看,莫扎特特别能帮助乐队塑造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
答:每一位听众听任何一位不同的作曲家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很正常的。作为一名指挥,从我的角度看莫扎特,我觉得如果了解当时的时代和莫扎特当时的表现形式、表现方法、他的思维,莫扎特是不难理解的。关键在于,指挥的格调和要求必须高,指挥要对原谱忠实,对细节有要求。比如说唱,一有legato就一定要唱起来,唱要到位,所谓到位,就是每个音都要做好,这是很难的。作为演奏家,要养成好的演奏习惯很难很难。世界上好的、有传统的乐团演莫扎特为什么觉得不难?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好的习惯,所以,他们一上手就是莫扎特应该有的音乐,也就是说,演得是对的,但好到什么程度,那就要看指挥的调教。如果只是把音符都奏出来,这样的莫扎特是最容易的,但有可能是最难听的莫扎特。
答:我觉得国家大剧院乐团虽然年轻,但他们这几年的进步真的是巨大的。大部分年轻的演奏家对音乐演奏风格已经有了很好的概念,这种概念如果持续下去就会形成好的习惯,这种好的习惯再过十年,到了作为乐队演奏家的最好的年华,应该就非常明显了,一定是行中的佼佼者。从这方面来说,我回国并不是只做一个指挥,而是想担当文化教育者的职责,并推动音乐活动和乐团运营的职业化和国际化。我们每个人都有离开岗位的那一天,但如果我能留下一个好的音乐传统和工作程序,我将时分荣幸。
我们回到莫扎特。还有一点我们要了解,古典音乐在莫扎特、海顿的时代,音乐的表现方式、乐队和乐器的表现力都是有限的。比如一个多愁善感的情绪,在古典音乐这里可能一带而过。这就像我们的古典诗词和现代诗的区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到了现代诗人这里就会是乱七八糟一大堆。古典音乐,一个句子就会概括很多东西,用一个legato代表一种性格都有可能。如果legato演不好,性格也就没有了。在莫扎特和海顿的音乐中,表现方法主要就是轻、响,legato、staccato,大而长的旋律没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句子拉得越长越高级,哪怕是简短的,你拉长了后也能形成一个长的句子和气口,听起来才会有更加优雅的句感。这都是需要指挥真正去付出的地方。莫扎特如果演得不好,从效果上来讲就会吃力不讨好。马勒演得再差也还是有效果,柴科夫斯基演得再差,也是效果不错的,对不对?因为最后反正是热闹着,但是热闹不代表质量。
答:技术上对于乐团来讲是另外一种难度,古典的难度。莫扎特那时候弦乐器用的是那种拱形的弓子,而且比我们现在的弓子要短。所以,莫扎特的句子和演奏法并不是写给现在的长弓的,我们在演莫扎特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弓段的使用,不是说大起大开大合,总是从弓根拉到弓尾,这是个错误,当时没有这个条件,莫扎特不是按这个去写的。这是弦乐的难度。管乐器方面,当时的双簧管和大管音量上都不够大,尤其是大管,连长号也就顶多是现在大管的音量。圆号好一点,长笛也没多大声音,它是木头做的。所以整个音乐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乐队编制和演奏法等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借鉴古乐器。我不赞同采用古乐器,但可以借鉴古乐器,它对于莫扎特音乐的演奏是有帮助的。
答:我觉得不存在本真演奏,真正的本真其实是音乐本身,并不是乐器。当时的古乐器有些地方可以作为今天演奏的借鉴,通过它们我们知道在莫扎特演的音乐里不要跳得太多,弓子要怎么拉、拉多少、弓速有多快,这些都可以借鉴古乐器。比如说古乐器的弓子没那么长,我们在拉慢板的时候不可能拉太慢,我们现在很多人把莫扎特的慢乐章拉得很慢很慢,是错误的。 莫扎特很少写lento(慢板),一般慢的乐章都写成andante(行板)、andantino(小行板),adagio(柔板)已经少见了。Adagio在意大利语中其实是没有这个词的,只有在音乐术语里有adagio,意大利语只有ad和agio,ad是助词,agio是名词,这两个词合在一起,意思就类似“随你舒服”,“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再口语一些,就像是“随您!随您合适!”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adagio并不是说一定要慢,它肯定是不快的,但它的更确切的意思就是悠哉悠哉,怎么合乎心意怎么来。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速度标记了解得非常透彻。
答:我赞同舒曼的话,我并不认为他的观点是过时的。没有比莫扎特的这个第一乐章那么优雅的了,其中有那种淡淡的忧愁,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诗意。但绝不是屈原,我认为屈原在精神上已经是晚期浪漫派了,这和他的楚文化背景有关。有一种观点认为楚文化有可能和西亚文化的影响有关系。莫扎特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一开始就惊世骇俗,中提琴的音型以前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当主题还没有开始时,音乐就已经开始了。这个乐章的忧愁基调可以说非常优雅,优雅至极,是非常古希腊的。第三乐章听起来非常具有悲剧气氛,但这是古希腊的悲剧,不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也就是说,这里的悲剧气氛没有发展,没有过分突出其中的任何一点,因为突出任何一点就形成了个人主义,而与个人主义相连的就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就没有了古希腊,就变成了李尔王。这个乐章的中部很诗意,回归到了自然和田园。在马勒那里也是这样,虽然音乐特别纠结、难受,让听的人也很难受,但是一回归自然,马上就非常美好。马勒和布鲁克纳的回归自然或回归宗教,可以追溯到莫扎特和贝多芬。因为自然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它的涵盖更广阔。你越是个人化,越极端,你所在的群体就越小。但是大自然是人人都喜欢的,在自然中,你的胸怀就广阔了。所以莫扎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从来没有过分纠结于自己狭小的自我,这是莫扎特的高境界。就像弘一法师那样看破红尘,世间酸甜苦辣了然于心,他可以展示给你,但他不是在向你诉苦,他展示给你是让你去感觉,让你去听,用最美的方式让你听。他给你讲一个悲伤的故事,但从来不会加上多愁善感的情绪在里面。这就是莫扎特的伟大之处。
我觉得21世纪对音乐的解释更注重个人的感受,有时会片面的强调某一方面或某一个点。但是,当年的舒曼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自己就既是作曲家又是音乐评论家,他看问题的高度和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所有,在音乐评论上,我们也要学习舒曼的态度,不能简单地说一种观点对、另一种观点不对,我们要去设身处地的思考为什么他们是那样的观点。
答:一点也不抵触。因为我觉得只有人世间所有的东西你都了解了、尝试了以后,你才能知道怎么能排出一个更好的顺序。莫扎特从小就旅行,和他的姐姐一起。他去过几次意大利,莫扎特有很多歌剧是用意大利语写的。意大利的用词,包括一些不雅之词,或者一些民间习俗的用法,莫扎特都学到了,这就是生活。你看《费加罗的婚礼》开始,费加罗和苏珊娜的对话中,费加罗和苏珊娜唱“Din, din”、“Don don”,圆号跟着吹“Bon bon”这就是在说故事。为什么这里要用圆号呢?因为在意大利语里,圆号是“corno”,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角。说一个人头上有角,就和中文里说一个人戴绿帽子一样。如果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corno”,就是给他戴绿帽子。所以圆号在这里一出现,肯定就有问题了。最后一幕,在花园里,费加罗说女人不可信,总是给男人戴绿帽子,圆号又吹响了,绿帽子一顶一顶送了过来。莫扎特是有很深寓意的,他的寓意来自民俗。因为莫扎特完全懂得这些世俗俚语,所以他都明白。但是他不停留在这些上面,他的格局和眼光是更高的。莫扎特以他自己的天分,将前人的音乐成就化为自己的,将他所了解的社会用最通俗的、世俗的同时又是最高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伟大的艺术。艺术来自生活,生活与艺术是相通的,莫扎特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的歌剧里写的伯爵啊这啊那啊男男女女们的故事,是在任何时代的生活里都能找到的。最重要的还是生活、内涵,就是说大家都能从莫扎特的音乐中找到一种生活的快乐和一种共同点。很多莫扎特同时代人的作品都很空洞,但莫扎特一点也不空洞。
王纪宴:乐评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吕嘉: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