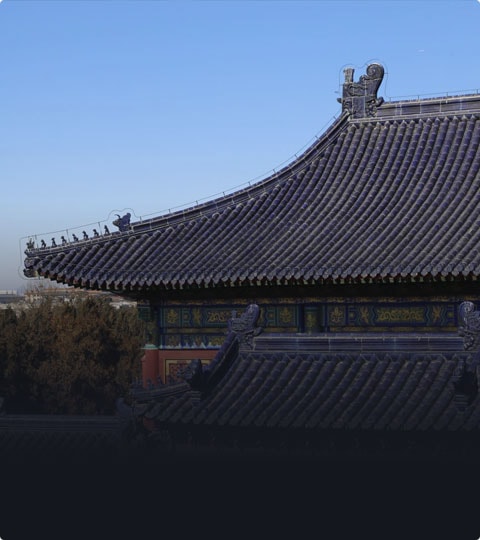菲利克斯·门德尔松是浪漫主义早期的德国作曲家、钢琴家、管风琴家和指挥家,他的很多作品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2019年是他诞辰210周年的纪念年,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即将在2019/20乐季中上演他的一些代表作,其中有他的第二和第五交响曲、小提琴协奏曲、《仲夏夜之梦》序曲等。
门德尔松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作曲家?我觉得舒曼对他的一句评语是很中肯的,他曾把门德尔松称为“十九世纪的莫扎特”。他还说,“门德尔松是一位最辉煌的音乐家,他最清楚地看透了时代的各种矛盾,并首次调和了这些矛盾”。他所说的“矛盾”主要是指古典的形式和浪漫的激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很多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身上都有,但在门德尔松身上尤为典型。他心中最重要的古典大师除了巴赫就是莫扎特。说他像莫扎特,主要是说他们都是早熟的音乐神童,而且都英年早逝(莫扎特35岁,门德尔松38岁),在门德尔松的音乐中经常流露出莫扎特式的优雅,形式结构也始终和莫扎特一样严谨。
门德尔松1809年2月3日出生于德国的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他的祖父摩西·门德尔松是德国启蒙时代的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曾主张宗教容忍和犹太人融入德国主流文化,门德尔松的父亲后来就皈依了基督新教,并成为一个银行家。在结婚后生的四个孩子中,门德尔松排行老二。母亲负责了门德尔松和姐姐芳妮(也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的早期音乐教育,门德尔松学习钢琴、小提琴和管风琴,还和姐姐一起加入了德国作曲家采尔特指挥的合唱团。采尔特是大文豪歌德的音乐顾问,与门德尔松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他成为门德尔松的作曲老师,并介绍门德尔松认识了歌德。他用巴赫的学生基恩贝格编写的旨在传播巴赫教学法的教材,使门德尔松在作曲上取得了惊人的进步,17岁时就写出了著名的《仲夏夜之梦》序曲,灵感来自莎士比亚的话剧(今年7月20和21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演奏他的这部杰作)。除了音乐,父亲还为门德尔松聘请了教文化课的家庭教师,学习了古典文学、历史、地理、数学和法语,使他成长为一个拥有全面的古典文化修养的人。
门德尔松生活的时代德国还没有统一。在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重新瓜分了势力范围。德意志邦联也开始在复辟时期(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旧秩序)推行一种保守主义的文化。门德尔松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形成自己的音乐风格的。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有四件大事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是他对历史上的早期音乐的关注促使他在1829年(20岁)重新上演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门德尔松仔细地研究了巴赫的乐谱,精心排练,终于完成了连他的老师采尔特都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第二件事是他从20岁起为了完善他的教育和趣味而周游列国,先后旅行到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特别是英国,他先后访问了十次之多,因而对英国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件事是在莱比锡完成的。莱比锡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地点。从26岁起直到逝世,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莱比锡,指挥那里的布商大厦管弦乐团(也叫“格万德豪斯管弦乐团”)。他每年要指挥20场系列音乐会(从10月到次年3月),还要加上名家到访、慈善音乐会和室内乐音乐会。门德尔松以不知疲倦的精力领导了这个如今的欧洲一流乐队。曲目的安排上显示了他对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偏好,他还上演了一些著名歌剧的音乐会版,节目单中混合了声乐和器乐,以及古典和当代的作品。第四件事也是在莱比锡,那就是他在1843年参与讨论了建立莱比锡音乐学院的计划。学院发表的公告说,这座学院将教授作曲、小提琴、钢琴、管风琴和声乐,还包括室内乐、合唱和音乐史的课程。学生来自德国和国外,要求他们参加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和其他市民音乐组织的排练和演出。教师包括门德尔松本人和舒曼等音乐家。1843年4月3日学院开张时有22名学生。这是德国最早的音乐学院,培养了大量优秀的音乐家。顺便说一下,挪威的音乐之父格里格和我国著名的作曲家萧友梅也都毕业于这所学校。
门德尔松是个多才多艺的人,除了作曲,他还是钢琴家、小提琴家和指挥家,而且他酷爱绘画,一生画了很多水彩风景画和素描。音乐和美术是相通的,门德尔松的很多音乐作品都堪称“音乐的风景画”。
1847年5月,在英国的繁忙演出后的回国途中,他得知姐姐芳妮逝世的消息,回到柏林见到姐姐的墓时,悲痛欲绝,不久他便中风,于11月4日晚因病情恶化而逝世。7日在莱比锡举行葬礼,抬棺人包括舒曼、加德、莫舍莱斯等音乐家。次日,他的灵柩被运往柏林,下葬于教堂墓地他姐姐的墓旁。
门德尔松一生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包括管弦乐曲、室内乐、键盘音乐、清唱剧和其他声乐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管弦乐曲,包括交响曲、音乐会序曲和协奏曲。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这个乐季中要上演的门德尔松作品大多属于这一类。
他一共写了五部交响曲,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在今年5月25日演奏他的第五交响曲(艾森巴赫指挥)。这是一部标题交响曲,叫做“宗教改革”,为奥格斯堡会议300周年(1830年6月)而作。两年后首演,作曲家死后于1868年作为第五号交响曲出版。从这首交响曲的首尾乐章我们可以听到两种宗教音乐的对立:基于莫扎特交响曲的朱庇特动机的帕勒斯特里那式的模仿复调写法和“德累斯顿阿门”的引用象征着天主教,而末乐章的主调和声织体的“上帝是我们的坚固堡垒”则代表了路德教。
1830年的意大利之行为他的“意大利交响曲”提供了素材,1833年在伦敦完成并首演,第二年修改,但在死后的1851年才作为第四号交响曲出版。开始的明朗主题犹如“欧洲南方的温暖而芳香的空气”。慢乐章开始的调式旋律显然在描绘宗教仪式或行进。第三乐章的灵感可能来自歌德的幽默诗“百合园”。末乐章标题为“萨塔莱罗”,开始的快速跳跃的音型使人想起他在意大利听过的萨塔莱罗舞曲。
1840年的“赞颂歌”交响曲在1841年作为第二号交响曲出版。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2020年1月17和18日演奏此曲。门德尔松像贝九那样在这首交响曲中引入了声乐,而且是宗教音乐,形成了一种交响曲和康塔塔的混合:三个乐章的乐队交响曲与九个乐章的声乐康塔塔结合在一起。来自圣经的歌词歌颂了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过程。
门德尔松的最后一首交响曲是“苏格兰交响曲”,灵感来自1829年的苏格兰之行,但直到1842年才在柏林完成。在爱丁堡的好莱如宫废墟中,当时才20岁的门德尔松孕育了开头的慢引子的主题,用低音管乐器和中提琴演奏。他在爱丁堡还出席了风笛音乐家的比赛,一些苏格兰民间音乐的元素无疑出现在谐谑曲开头的五声音阶的活跃的单簧管主题上。全曲共五个乐章,通过让曲中的很多主题材料都来自慢引子的基本动机(E-A-B-C),他让这部作品的整体很统一。
此外,门德尔松早年还创作过一些弦乐交响曲,从1821到1823年写了13首。这些作品显示出巴赫,特别是他的二儿子C.P.E.巴赫的弦乐交响曲的影响。
门德尔松的音乐会序曲是他最流行的管弦乐作品。他一共写了六首独立的序曲。1828年创作的《平静的海与幸福的航行》是其中之一。门德尔松此曲以歌德的两首短诗为题材,表现一条船飘浮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贝多芬以前为这首诗谱写过适于合唱团与乐队演出的短小的康塔塔(1822年出版),而门德尔松则只用乐队来表现这首诗。序曲由两幅“图画”组成,由一个过渡段连接。一个尾声补充了“幸福的航行”,暗示对船只抵达港口的欢呼。
门德尔松还有一首标题性序曲也很有名,那就是《赫布里底群岛》,创作的灵感来自1829年他在苏格兰西海岸的旅行。他再次从一个动机引出他的主题材料,生动表现了海浪的汹涌和海景的奇特。1833年钢琴二重奏的改编曲出版时他还用了《芬加尔的洞穴》这一标题。
门德尔松的协奏曲作品集中在他自己擅长演奏的两种乐器上:钢琴和小提琴。他发现协奏曲的创作在他的一生中是一项特别艰苦的工作,他向朋友们承认,他痛苦地在炫技的要求和艺术作品的整体性之间做出协调。他的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比较有名,钢琴写作以明亮的、辉煌的各种技巧为主,但很少使用流行的钢琴效果。
他的最后的一首协奏曲很特殊,那就是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它是19世纪小提琴协奏曲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三个乐章相连,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包括第一乐章独奏的提前进入,华彩段的位置用来连接展开部和再现部。三部曲式的慢乐章提供了一首抒情的“无词歌”,回旋奏鸣曲式的末乐章,是典型的门德尔松的狂想曲式的谐谑曲。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在7月21日由庄东杰指挥,何子毓演奏这首名曲。
门德尔松的室内乐作品也很优秀,主要有三首钢琴三重奏、四重奏、小提琴奏鸣曲、六重奏、八重奏(1825年完成,被认为是门德尔松的第一部杰作)、六首弦乐四重奏(1827-1847)、两首弦乐五重奏等。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室内乐系列将在2019/20乐季中呈现作品44号中的两首弦乐四重奏,它们创作于门德尔松1837年婚后在弗莱堡和黑森林度蜜月期间,有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
门德尔松一生都在创作钢琴音乐,但对他那个时代的钢琴音乐他又保持了一种又爱又恨的态度,摒弃了很多时髦的技巧。在他的成熟作品中有三种影响很突出:巴赫的对位法的活力,贝多芬中晚期的戏剧性姿态和超越的语言,以及韦伯的才气焕发的钢琴织体。《无词歌》是门德尔松最流行的钢琴作品,1832年至1845年间出版了六卷,共36首(还有两卷死后出版)。当时的一位理论家A.B.马克斯的音乐思想(探讨了器乐的表现潜力)也影响了门德尔松。或许作曲家在最初创作这些作品时曾写过歌词,然后又把歌词去掉了。当有人建议他使用一些标题或填词时,门德尔松回答说他想保持原样。他觉得没有标题和歌词的纯器乐更有表现力,更不受限定。他只对其中少数几首加上了标题(如三首威尼斯船歌)。
门德尔松不是19世纪唯一的复兴清唱剧的作曲家,但他的两部作品:《圣保罗》(1836)和《以利亚》(1846)是他那个时代唯一持久流行的清唱剧。当然,从扫罗到保罗的改宗这个题材对拥抱基督信仰的门德尔松家庭也有特殊意义。在创作上,他向亨德尔学习了很多东西。《以利亚》表现《圣经》中的著名先知,运用了丰富的合唱手段,取消了叙述者,让角色自己陈述戏剧情节,音乐结构也更加严谨。
门德尔松还有一首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是世俗康塔塔《第一个沃布尔加之夜》(1832)。它以歌德的诗歌为基础(出自《浮士德》的第一部分),表现春天布罗肯山上的异教徒的祭礼。虽然门德尔松没有写过一部成功的歌剧,但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歌剧脚本。他还写过一些戏剧配乐,最有名是1843年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谱写的12段配乐(包括著名的婚礼进行曲)。
总之,门德尔松在19世纪30-40年代(浪漫主义早期)站在德国音乐的前沿,是一位第一流的作曲家。他的音乐风格在20岁前便已形成,主要的影响来自巴赫、莫扎特,以及贝多芬和韦伯。他看似保守的风格使德国古典音乐的伟大传统在浪漫主义的新时期再现辉煌。在这方面,他与更加激进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例如瓦格纳、柏辽兹和李斯特等人是有所不同的。不过,对门德尔松的接受却也经历过曲折的历程。尼采认为他只是德国音乐在贝多芬和瓦格纳之间的“一个插曲”。在他死后,人们经常对他的音乐加以曲解,使之变得越来越感伤化。他还特别受到欧洲19世纪以来的反犹主义的伤害。瓦格纳在他的匿名文章《论音乐中的犹太性》中批评过门德尔松。20世纪的纳粹更是禁止了门德尔松的音乐,移除和摧毁了莱比锡布商公会大厦门前的门德尔松雕像。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门德尔松的伟大,庆幸的是,如今的人们对他有了更准确的认识,他的音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喜爱。